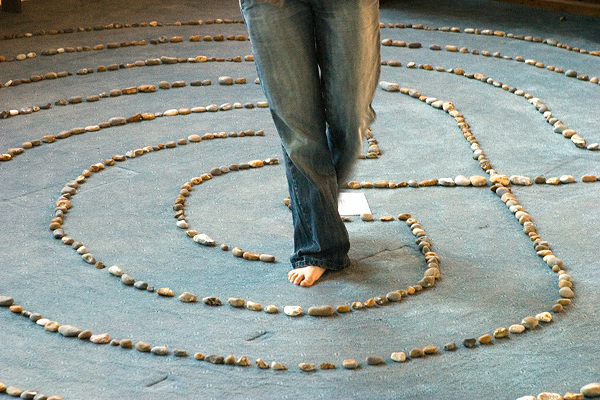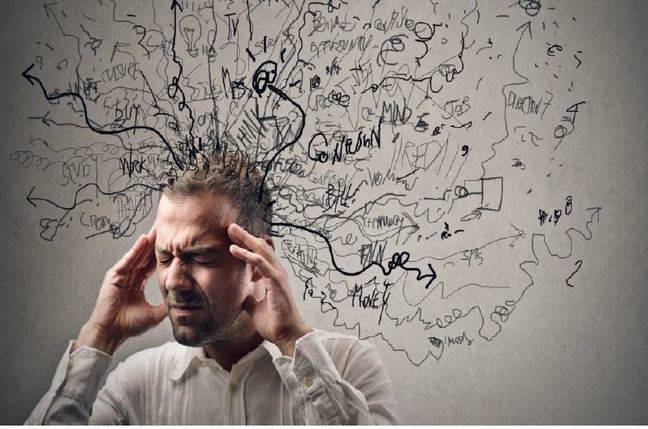在瑜珈課上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動作習慣。(呃,我知道,瑜珈課不應該是用來看其他人的場所,但我是瑜珈老師,在前面給指令的那個傢伙,不管我喜歡或不喜歡,總是得把眼睛仔細盯著每個同學的身體。)
給個指令要大家站在山式(tadasana),有的同學會像是訓練有素的士兵一樣,用力挺起胸膛,雙臂往外側旋轉到掌心朝前。要大家慢慢加深呼吸,有的同學馬上肚子鼓漲(所謂「腹式呼吸」的餘毒?),或者聳肩,或者骨盆前傾。
光是一個雙手往上延展的動作(urdhva hastasana),有的人兩隻手十隻手指頭非得緊緊閉上才能開始動作(也有的人相反,非得十隻用力撐開);有的人永遠兩條手臂往側邊或者斜四十五度,也有的人只習慣往正前方移動手臂;有的人手還沒舉到一半,下巴就急急忙忙高高抬抬起,有的人是聳高肩膀,有的人不自覺翹起屁股,有的人腳掌的重心整個往前移到腳跟幾乎要飄起來。
要進入站姿前彎(uttanasana)也一樣變化多端。有的人得先雙手在胸前合什;有的人才剛剛彎身,膝蓋就先往後推;有的人不由自主整個過程都是抬起下巴、脖子後側緊縮;有的人愈彎愈深,腳趾頭就愈抓愈緊。
Feldenkrais Method 的創始人 Moshe Feldenkrais 對於這類的動作有個非常生動的形容詞:寄生蟲(parasitic)。就像寄生蟲寄生在宿主身體上,「寄生蟲動作」(parasitic movement),寄生在「宿主動作」(host movement)上,隨著時間的催化,兩者愈來愈不可分割。最後,本來想做的動作,就變成必然伴隨著「寄生蟲動作」了。
寄生蟲,顧名思義,是由宿主來提供養份。也就是說,必然會耗損宿主的能量,甚至危害宿主的生命,導致宿主死亡。
我們在日常生活的運作上,不自覺地豢養了多少寄生蟲動作呢?
回到最基本、最重要的動作,也就是分分秒秒應該都在持續進行的呼吸來觀察看看。
躺在瑜珈墊上(或者任何穩定的地板,可以的話,別在床墊上練習),彎曲膝蓋,讓雙腳自然輕鬆平放在墊子或者地面(是的,我知道,「自然輕鬆」這個指令,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是莫大的難題了,如果是這樣的話,反正就是讓雙腳能夠放在地面,別用力就是了)。忘記一切學過的呼吸方法(不論是胸式、腹式、橫膈膜,全都先放下),告訴自己,「這不是比賽」,「這不是考試」,能不用力就不用力。觀察自己的呼吸是怎麼進行的。觀察自己的脖子、肩膀的連鎖反應,觀察自己前胸後背的細微運動,觀察整條脊柱形狀的變化,觀察肚子和骨盆有哪些動作,觀察任何觀察得到的現象。
有沒有可能更不費力一點?有沒有可能,讓呼吸更輕鬆自在地進行?
休息一會兒之後,再回到舒服的坐姿或者站姿。重新觀察自己的呼吸,並且和剛剛半躺時的身體狀態比較看看,有哪些差別。
這些都可能是我們花了漫長的歲月、耗損莫大的能量所豢養出來的寄生蟲啊!
而且不只動作上會有寄生蟲,思考習慣、情緒反應也有寄生蟲。
以往的年代,家家戶戶吃飯的時候,總是得配電視,現在則是配電腦、手機用餐。(「電視」、「手機」是一道菜嗎?好吃嗎?能吃嗎?)彷彿沒開著電視、沒盯著電腦或者手機螢幕,就吃不下飯。看著這些動態的畫面,不自覺得情緒高漲、澎湃起伏,一會兒想打人,不一會兒又邊哭邊笑。
這些心理、精神層面的寄生蟲,又會誘導、活化肢體層面的寄生蟲。於是,該好好讓消化系統運作的時間與能量,又讓寄生蟲吃光光。
從這個角度來看,靜坐還真是絕佳的練習。每天花一段時間,暫時排除肢體的動作,先安頓下來外在的形狀,專心觀察呼吸上。別擔心抓不到蟲,不用三五分鐘,不需要想的,不需要講的,不需要擔心的,不需要期盼的,形形色色所有寄生蟲通通都會蠢蠢欲動,都會現形出來。
怎麼應對?很簡單,別再拿時間、能量去豢養這些寄生蟲。別跟著寄生蟲起舞。我們可是「宿主」啊!把時間、能量帶回到呼吸上。(還記得前面半躺時的觀察呼吸練習嗎?) 要當主人,就要有真的當家做主的自覺與風範,拿回呼吸的主導權,拿回身體的主導權,拿回精神的主導權!
同樣的原則,當然也要帶回瑜珈墊上。慢慢來,仔細觀察自己怎麼做下犬式,身體的哪些部位還可以少點壓力,還有多少該丟掉的寄生蟲,特別是很多人經常痠痛不已的肩頸、下背,或者自己日常生活中最容易不舒服的部位,多留神看看,細細微調實驗看看。下犬式這樣慢慢做、細細做,其他動作當然也應該要這樣對待。
然後咧?當然就是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囉!
(對了,上次有同學提到關於「課後作業」的事。噹噹噹,作業來囉,很簡單的:花十分鐘看臉書吧。什麼?這麼簡單?不是啦,花十分鐘,觀察自己在看臉書的過程,能抓到多少寄生蟲。拿出紙筆出來,一項一項寫下,不管是肢體上的寄生蟲,或者思考、精神、情緒上的寄生蟲。寫下來,然後把紙折好,收起來。再花十分鐘看臉書,實驗看看,能不能在 bug-free 沒有蟲的情況下輕鬆完成。不行的話,那就先關上臉書,找個地方躺下來,重新再做一次前面說的呼吸練習!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