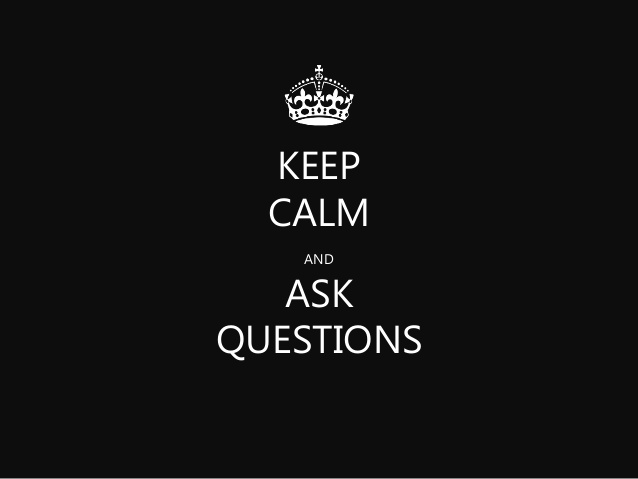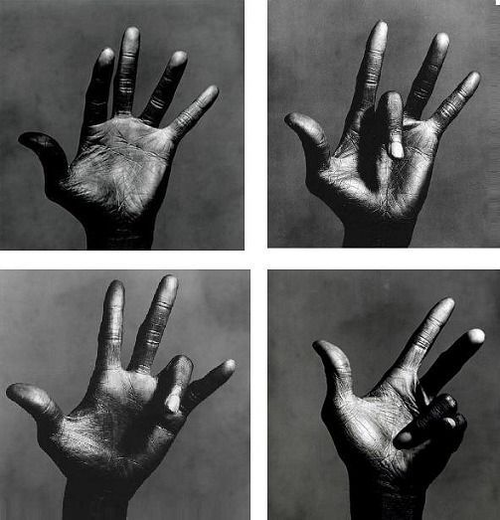如果問,「想不想要整個人都放鬆?」幾乎很少人會回答不要。就好比問,「想不想要變得好有錢?」也幾乎很少人會回答不要。
但實際上,即使某個人真的很想很想變得好有錢,通常也就是停在「很想很想」,訊號微弱的念頭(說不定連自己都不怎麼相信),而沒有化成真正的行動,有效率的行動。這種「想」,差不多只是「希望」、「盼望」的層次上而已。
「想不想要健康的身體?」「想!」「有多想?想採取哪些行動讓身體更健康?」「嗯,沒怎麼想過這些問題耶。」
一般人的「想」,通常比較常是「期盼」,甚至就是「許願」、「向宇宙下訂單」。
「最好是讓我中個樂透,瞬間就變有錢人。」
「如果每天都能讓人按摩個一小時的話就好了。」
「等這個階段的工作告一段落,我就要開始練習靜坐了。」

等著外在神奇的力量出現,等著外在環境的改變,等哪天「一切條件都準備好了」。
我昨天的放鬆是這麼操作進行的:坐在餐桌前,好好讀了兩個小時的書,電腦裡的電子書。
通常我在閱讀諸如 Alexander Technique、瑜珈、佛教的內容,會比較有身體的自覺,意思是,會讓自己的身體少一些壓力,特別是肩頸。所以坐在我對面的老婆大人可以從我的坐姿,判斷出我在讀哪一類的文章或書籍。
昨天並不是。
在歷經了「母親節的逆襲」之後(因為是母親節,上課人數縮水,街上的餐館爆滿,只得在下課後趕緊閃人回家),我們乖乖躲在家裡吃晚餐。白天的情緒似乎還沒完全過去,我知道身體還在微微緊繃的狀態。
「等一下碗給你洗哦!」接到指令之後,我開始盤算,要輕輕鬆鬆好好洗碗,再沖一杯咖啡,接著就來看書。
目標設定好之後,洗碗的過程就像是大休息前的舒緩動作,一個一個盤子、碗、湯匙、鍋子,一個一個慢慢來。洗著洗著,已經放鬆了一點。
沖咖啡和喝的過程差不多就是大休息了。(果然,在自己家裡沖的品質,常常都遠勝外頭店家的名貴單品啊!)勻勻地沖,慢慢地品嘗,讓咖啡的前味、後味有足夠的時間發散出來。好像靜坐前的 body scanning 一樣,該鬆的都讓他們鬆吧。
比較不一樣的是閱讀的準備。我抓了三四本書,墊高筆記型電腦。(雖然我很常教同學們這招,但自己也不是每次都會乖乖執行,不過昨天閱讀前就先設定好要放鬆的目標,順手也就擺設妥當。)
剛開始讀的時候,還稍微調息了一陣子。確認肩頸鬆開,確認胸腔上下左右前後都能一起順暢呼吸,慢慢讓整個身體都一起進入狀況,差不多就是靜坐一樣的練習吧。
閱讀。
好像除了站起來倒兩次茶水之外,就是輕鬆坐著兩個半小時左右專心閱讀。吸收了不少非常棒的觀念,而且整個過程,大概也都還時不時可以感受到呼吸的狀態,肩頸、軀幹、四肢的狀態。
非常舒服,非常享受的一段閱讀過程。我知道自己整個人都放鬆開了。身體知道,身體會說;情緒知道,情緒也會說。
理論上,所有活動都可以用這種方式進行才對。但只是理論上。
因此我們得練習。運動也好,練習瑜珈、靜坐等等技巧也好。不過練了老半天,還是得拿出來使用,得真的派上場,操作、試驗。
別只是停留在「期盼」式的「想望」。真的想,就不斷練習,設定好目標,然後就動手玩看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