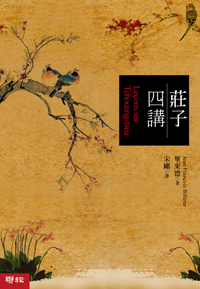很多人練體位法的方式,和一般人做運動沒什麼差別:該用力的肌肉或者用不上力 、或者用了太大的力;不該用的肌肉不聽使喚,察覺不到,一不留神就使盡全力,繃得緊緊的、或者縮得緊緊的。

特別是肩頸。
現在的人本來就很辛苦了,一天到晚看著電腦螢幕、手機,肩頸的狀態就不太理想了。帶著疲憊的身軀,下了班之後再趕到瑜珈教室,強打起精神,老師一個口令下來,就拼了命地完成動作,更不容易發現自己慣常的使力方式全都出來了。
就這樣,雖然一直在「練緰珈」,但仍然三不五時得去讓整脊師父調整調整(chhiâu-chhek chhiâu-chhek),或者油壓指壓精油芳療按摩。
有沒有可能不那麼用力?

看看上圖裡左下方看著報紙的阿伯,再看看其他低頭看著手機的乘客。發現什麼不同了嗎?
這樣試試看吧:先換個位置,離開電腦螢幕一下。找另外一張椅子坐下來,拿起手機,停留個半分鐘,然後觀察看看自己用力的習慣。有沒有可能不那麼用力?再試一次看看,特別是肩頸,有沒有可能不那麼用力?
憶余初學此拳時。楊澄師每日囑余曰。要鬆。要鬆。有時又曰。不鬆。不鬆。時或戒之曰。不鬆。便是挨打的架子。極其至。則曰。要鬆淨。相繼何止複數千遍。余於兩年內。聞此語。甚至覺頭大如斗。自恨愚蠢。抑何至此。一夕忽夢覺兩臂已斷。醒驚試之。恍然悟得鬆境。其兩臂所繫之筋絡。正猶玩具之洋娃娃。手臂關節賴一鬆緊帶之維繫。得以轉捩如意。然其兩臂若不覺已斷。惡得知其鬆也。 (《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》)
或者換個方式,站起來試試。就只是站著,可不可能兩條手臂都不用力呢?可以的話,往上伸展時,能不能也不用力呢?或者,來個 ardha uttanasana,能不能讓胸口輕輕打開,但是維持著兩條手臂都只是輕鬆掛著?

不那麼用力,真的很不容易。連太極拳宗師級的鄭曼青,在面對自己老師教導時,都還會覺得自己「愚蠢」,一天到晚被老師盯著。別在意,心情放開一點。
以前我常常和家裡的貓玩一種遊戲。他輕鬆躺著,我輕輕玩著他的手掌。在他心情放鬆的時候,手掌的關節根本就是我要怎麼轉就能怎麼轉。這種時候,我常常會和他說,「手熟是誰的?手熟不是你的哦」。後來有一次我自己在練習時,忽然想起這遊戲中的台詞,我默默地告訴自己,「手臂不是我的,手臂不是我的」,然後,真的愈來愈鬆了點。但一不專注,肌肉微微緊繃的感覺又瞬間浮現。
好像在練 Alexander Technique 一樣。腦子下達自己設定要的命令(例如:「我的肩膀肌肉不要用力」),希望可以練習到 “The mind moves, the muscles follow” 的狀態。愈專心,成效就愈清楚。
好像在練靜坐一樣。因為專注在呼吸上,心緒得以集中不渙散,所以才會有輕鬆、舒暢的副作用。因為一直專注在呼吸上,所以愈來愈穩定。要放掉不抓緊的肌肉比較容易放得掉,想看的事情比較容易看得清。
要言雖不繁。然真能領悟。卻不簡單。非信之誠。行之篤。縱能領悟。亦不能抵於成。(《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