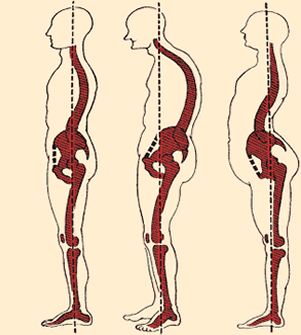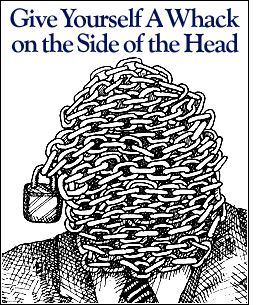我們總是多少有些什麼毛病、症狀,在身體這個那個部位,在這種那種情緒裡,在這般那般的思考模式中。
有的人長期背痛,有的人時不時肩頸痠,有的人呼吸不順(甚至會有「忘了呼吸」的狀態出現)。
有的人兩隻腳掌就是沒辦法好好站在地上,有的人總是骨盤歪斜外加前傾或者後傾,有的人始終脖子往前方伸長讓頭一直處在軀幹前方。
有的人沒辦法安靜個三五分鐘不說話,有的人三五分鐘不摸到手機滑一下畫面就焦躁不安,有的人在人群前就興奮異常,有的人只想躲在角落一邊無意識地畫小圈圈一邊覺得自己好可憐。
有的人白天提不起精神,有的人夜晚無法入眠,有的人整晚睡著覺一直在做夢,有的人白天沒睡覺也一直在做夢。
然後我們試著看醫生,西醫看完看中醫,中醫看完看民俗、另類療法,接著拜拜求神求佛求上帝,算命排生命靈數排塔羅,咒語從漢語唸到梵語唸到藏語唸到夏威夷語(聽過 Hooponopono 吧?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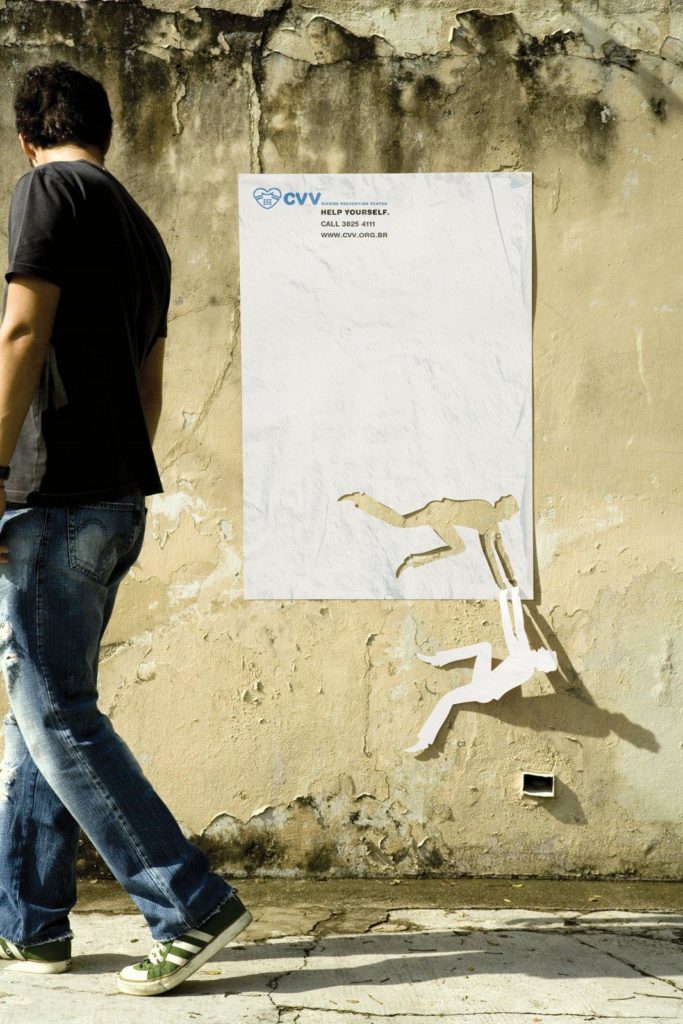
source,也請參考「解脫道上不會有伴,就你自己。」這篇文章。
也有的人剛好接觸到瑜珈,也有的人高舉著「療癒」的旗幟在賣瑜珈。
瑜珈好像的確有些「療效」,不是嗎?要不然為什麼我們要辛辛苦苦地下完班、週末假日還抽空來折磨自己?
回想看看上一次去按摩(或者推拿、整脊)的美好經驗,整個人慢慢地鬆開來,肌肉、筋膜、神經、情緒。但可能在回家的路上,在隔天睡醒下床之後,在一陣辦公室緊張的作業、操勞不停的家事工作之後,那些美好的體驗全然消逝無蹤,不知道躲到哪去了。
當然很多時候,瑜珈課帶來的效果也差不多是這樣。
我們還沒理解清楚其中的關連,道理,因果關係。我們還在嘗試去理解自己究竟是用什麼方式在使用身體,用什麼方式在思考,用什麼方式在看待情緒。
我們想繼續探究、挖掘進去。我們試著在這個前彎或者後彎裡實驗看看,我們試著兩腳或者單腳站著看看,我們試著倒立看看,我們試著暫停吸氣吐氣一小段時間看看。
我們試著靜坐看看。
光要坐著十來分鐘就不舒服了。下背痛,膝蓋痛,呼吸不順,腦子完全靜不下來啊。
因此,我們繼續學習一些技巧,什麼樣的坐姿才舒服,才不費力。哦,原來如果骨盤不前傾,不後傾,整條脊柱好像就比較自然可以順利延伸,呼吸好像就比較輕鬆了。哦,原來如果先活動活動髖關節、肩關節,坐著的時候彷彿可以比較不費力掙扎。哦,原來如果能夠持續維持一兩個星期、一兩個月的簡單運動,早點睡,吃飯別吃到撐飽肚子,靜坐的過程似乎就少了很多阻礙,順利許多。
把注意力從腦子的跳躍思考,切換到觀察、感覺自己的身體,呼吸說不定就慢慢穩定一點。呼吸穩定一點之後,腦子也就鬆了一點;腦子鬆了一點,呼吸又再變得更勻更順。
突然,我們意識到,咦,下背好像這陣子比較不痛了,睡眠的品質似乎也改善了一些。
這些「療效」並不是來自瑜珈老師的口令,不是來自老師調整你身體的那雙手,也不是來自宇宙的神奇能量。
這些「療效」是瑜珈練習過程正常的副作用。有的人練個三五個月會開始慢慢察覺到這些副作用出現,有的人得花久一點的時間。但也有的人練著練著,一不小心,把副作用當成主要的目的。
那主要目的是什麼?我哪知道啊。
* Leslie Kaminoff 最近修改了他前幾年前的那篇文章 I’m Not a Yoga Therapist Anymore,重新刊出,很值得同業或者有志於從事這一行的朋友們仔細讀讀,仔細想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