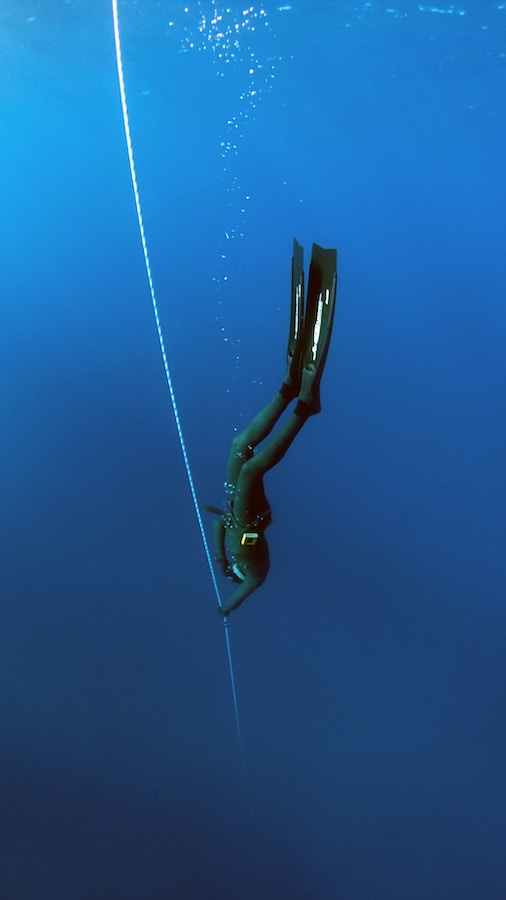「是多餘的緊繃吃掉你的力氣。省下來,動作就變輕鬆了。」「不是你的肌力不夠,不是你還得再練重訓才夠力,而是腦子裡的資源分配、協調的技巧要更熟練!」這不是哪一個門派、系統的瑜伽課,這裡也沒有標榜科學研究、解剖學、生物力學、肌動學的術語。這裡是 KT Lab 平常的米克斯瑜伽課。
常常有新認識的朋友或者同學會問我(通常可能有上過幾次瑜伽課的經驗),「聽說你是瑜伽老師,那請問你是教哪一派的瑜伽?」前一陣子和朋友一起爬山,朋友碰巧在步道上他們的朋友,大家一起邊走邊聊。新朋友在大瑜伽會館練過各種流派,問了我一樣的問題。我笑著回答,「我教的是米克斯瑜伽。」對方聽不懂,我再繼續解釋,mixed, hybrid,混血兒的意思。
很多愛貓愛狗人士都知道,混種的毛孩子比較不會得到純種貓狗常見的遺傳基因病。
這位朋友有點椎間盤的狀況,目前正在做物理治療。剛好大家停下腳步歇會兒,我看了他的站姿,骨盆果然有不自覺的前傾,就順口講了一些簡單的自我觀察、自己調整的觀念和方法,也很快示範了一兩個小動作。我說,「這也是瑜伽,米克斯瑜伽的應用。」
在自己的小教室裡,有時候四五個人的一堂課,同時來了兩位肩膀受傷的同學,左右肩各一個。或者年紀大一點的媽媽(像我媽媽一樣的歐巴桑),她可能前兩天上的是太極拳,明天晚上要跳國標。前一陣子還有不少年輕媽媽,剛懷孕的,快生產的,或者每天二十四小時蹓小孩陪小孩幾乎不得喘息的。當然更常碰到心情鬱悶的,上司、客戶、帳單、結案報告等等壓力大到不行的。
這些同學來上課的共通點,大概都希望能夠藉由簡單的肢體活動,藉由好好深呼吸,享受一段專心和自己身體相處的時光。最好一堂課下來,肩頸、下背的痠痛緊繃釋放個三五成或者七八成,或者能夠在大休息裡進入深沉的放鬆、休息。
真是非常幸運,而且非常感謝的是,來我這邊上課的同學,通常並不太在乎我這個老師教的是哪個門派、哪個系統,有沒有去過印度進修,也沒有人在意這個動作是不是、夠不夠「瑜伽」。
老師用不用梵文名字講動作,同樣也不會有人理會。
有時候同學也會問,這個或者那個鬆肩的動作,是從哪兒學來的。很可能我根本回答不出來,在腦海裡思索半天,好像有點像某個瑜伽動作的變形,好像有點像 Feldenkrais Method 的某堂 Awareness Through Movement 裡練過的主題,好像又有點夾雜 F. Matthias Alexander 還是楊澄甫還是鄭曼青還是哪個老師講過的心法,又好像是上次自己玩某個動作時轉出來的?

換一種比喻來說。走在山裡人工刻意裁培的柳杉純林,乍看之下,美則美矣,但在純林裡多走個一二十分鐘,就會發現整個環境怪怪的,非常不自然,連一點蟲鳴鳥叫的聲音都沒有。原因就是純林的環境裡生物多樣性一定比天然林低。多走個幾次,大概就不會只看見人工純林表面的美而已。
說不定我們的肢體、知覺練習也有類似的道理在其中。
我還是很愛練拜日式,或者最常見的那些瑜伽動作。但我也很愛在拜日式前或者拜日式後串接意想不到的動作,或者更有趣的是,可以怎麼變化成不一樣的內容組合,但仍舊保有拜日式的內涵、要素。
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玩著玩著,會玩出不一樣的東西。而且,並不見得是因為想著,「如果要更釋放三角肌、上斜方肌、提肩胛肌,我是不是應該要這樣那樣做?」,也不是每一次都在仔細計算著,「要是這個動作改成那樣做,會不會就讓下背更放鬆,會不會讓髖關節能做更大的動作?」
有時候就只是好玩。可能是順著天氣變化,順著情緒,順著意想不到的靈感,「那不然就這樣玩玩看?」的念頭才閃過,我整個人就在地板上又翻滾了一圈,滾完才發現,「嗯,還蠻好玩的嘛」。
或者有時候是上課到一半,我直覺感受到「好像什麼地方卡著了」,可能是某個同學的膝關節,可能是某個同學的情緒,可能是教室裡的「能量」(咦,我也是會用這個詞嘛)。這種時侯,我也常在心裡鼓勵自己,「那不然,就改個方式玩一下看看吧!」
反正我們是米克斯,我們可以有更大的即興的空間。
之前讀過舞蹈家許芳宜在描繪她的老師對她的影響時,說了這樣一句話:「創作如果有標準答案,應該就不會那麼吸引人了吧!創作如果只能跟著理論規則,應該也不需要創作了。」
我們不必得是舞蹈家、藝術家,也可以抱持類似的態度來看自己的練習,像是創作一樣的練習。沒有標準答案的練習方式,跟著自己的身心需求而調整,而不是永遠只是亦步亦趨仿效這家那家的模樣,畫別人家的葫蘆。
米克斯瑜伽也好,甚至,米克斯練習,都好。
我的練習,我的歷史學的知識都告訴我,從來就沒有「原汁原味」這種事。太極拳沒有,瑜伽也沒有。也不需要把力氣花在找尋某種想像的、一成不變的典範。
我練的,我教的,就是米克斯的瑜伽,米克斯的練習。我自己揉合出來的 style。
在教室裡就著那一大片鏡面牆壁自己一個人練習的時候,我時不時會問自己:我是不是又掉進一種我自己創造出來的新窠臼了?
一起來繼續玩出新的可能吧!
延伸閱讀:
按部就班,即興演出
框框是用來跳出去的!
[關鍵字系列] 不要輕易為自己定型:anattā 是一種操作型定義、行動指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