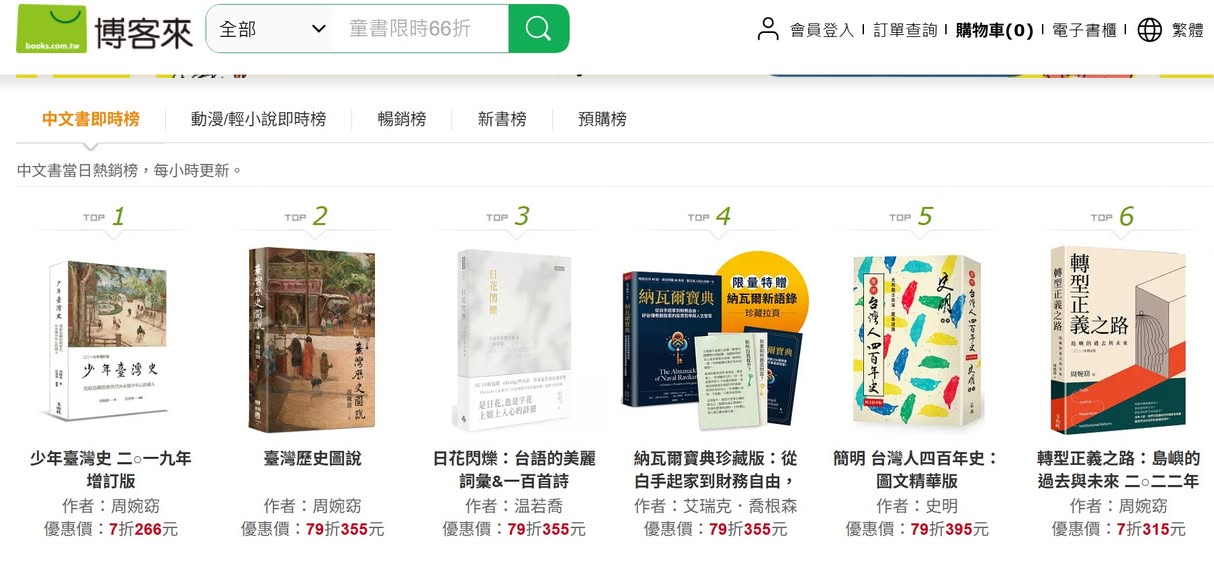很多人問我,如果只能選一種運動繼續練,會是哪一種?
我的答案:小孩子才做選擇。我覺得重要的、好玩的,我都要。
我的身體練習從瑜伽開始,練到以教瑜伽為工作,邊練邊教的過程,也嘗試各種其他運動、其他練身體的方式、系統。
結論先說。這二十年來練習的經驗,讓我認識到練身體這個領域真正值得長期投入的三本柱:重訓、跑步、瑜伽。但我想說的,不只是這三個名字。
這個世界每隔三五年就會有一股新風潮。能引領風潮的,背後都自有道理,只是哪些風潮三十年後還在,很難說。
我們現在練的瑜伽,在二十世紀七八○年代進入歐美,再從歐美流傳到全世界(甚至回銷到印度),算是歷久不衰的身心練習。長距離慢跑從美國流行再推廣到全世界,也已經是二三十年以上的穩定風潮。而這十年真正改變運動世界版圖的,是重訓。有運動科學做後盾,有全世界大量的實踐者用身體驗證,這股風潮確實不可小覷。
這幾年我看書、看影片,也實際下場練。結論是:重訓、跑步、瑜伽各有其不可取代的特點,但若只選其中一項、只著重單一面向的活動,恐怕都不夠。
重訓偏向肌力與結構,跑步偏向心肺與耐力,瑜伽則在兩者之間提供另一個維度,身心整合、動作控制、呼吸意識,還有一件事後面再說:活動度(mobility)。三者並非對立,而是互補。就像光譜裡紅橙黃綠藍靛紫之間,沒有一條清楚可辨識的界限,彼此滲透,彼此支撐。這就是我說「三本柱」的意思:不是三條平行線,是一個互相撐住的結構。
這幾天大家在瘋棒球,我想到日本隊山本由伸的例子。這位技壓大聯盟的世界頂尖投手,但他的訓練方式裡,重訓的比重極低,核心是瑜伽和皮拉提斯,常見的招牌動作就是輪式和倒立。他練習的不是讓身體看起來更強壯結實,而是對身體細節能精準控制,更靈巧地達成各種活動的要求。
有一種說法是,什麼運動都好,只要你天天都期待去練,就是好運動。這話沒錯。但年紀愈大,就愈不容易靠一招應付所有層面的需求。就像不可能只吃肉、只吃蛋、只吃蔬菜水果就長久健康,飲食需要均衡,動作練習也一樣。
只是光說「都需要」,問題並沒有解決。事情還是有先後順序,輕重緩急。
還不太會走,最好別急著跑。連徒手蹲都不順不穩,連骨盆和脊椎怎麼維持中立位置都還沒概念,請先別急著要負重深蹲。
所有動作練習,不外乎是用肉身對抗地球重力,或者順勢協調、省力活動。人是兩足直立動物,最基本的動作變化還是以站姿為主。把基本的站姿練好,呼吸帶領動作的方式搞清楚,後面不管要往哪個方向練,都有根。
這些,我稱之為「基礎」。也是我們教室每天都有基礎課的原因。
以瑜伽做為入口,不只是因為瑜伽涵蓋自體負重的肌力與肌耐力,也包含跳躍等串連動作來強化心肺。更重要的還有呼吸,這是瑜伽練習裡的核心關鍵所在。在我們教室,天天都會練如何好好呼吸,但不會刻意標榜「腹式呼吸」或「橫膈膜呼吸」,而是回歸輕鬆、順暢、有效率的呼吸本身。
教室裡不時有從來不曾運動的同學來。我的建議一律是:先上一陣基礎課再說。呼吸先順,核心意識先建立起來,能在不同條件下讓骨盆回到中立位置。之後要跑要跳、要怎麼舉重若輕,都好說。
但在這些表面容易拿捏、看得到的東西之外,瑜伽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核心概念:mobility(活動度)。
柔軟度和活動度不是同一件事。柔軟度是被動的,通常指的是的是放鬆狀態下身體能到達的範圍。活動度是主動的,你能在控制之下,把關節帶到多大的範圍裡活動,再安全地回來。很多人以為瑜伽就是拉筋,就是把自己折來折去,那只是最表面的。真正的活動度訓練,是在整個動作範圍裡都保有力量與意識。
我愈練愈覺得,mobility 不只是身體的事。
靜坐的練習,讓我開始理解另一種活動度:心靈的活動度。我們的頭腦平常高速運轉,思緒拉著我們到處跑,很少有機會慢下來。靜坐練的,就是這個降速的能力。不是讓大腦停下來,而是讓大腦學會換檔,從高速進入低速,再進入安靜,需要的時候再重新啟動。
這讓我想到 HRV(心率變異性)。HRV 高的人,心臟能在壓力與休息之間快速切換,不會卡死在某一個狀態裡。心靈的活動度,有點像是心靈的 HRV,能緊能鬆,能快能慢,能在高壓之後真正放下來,也能在安靜之後重新全力投入。
這種能力,同樣需要練習。而練習這件事的前提是,必須先知道自己現在在哪裡。關節現在的位置、動作的邊界、此刻心靈的狀態是緊還是鬆、是專注還是渙散。沒有這個意識,活動度可以只是帶來危險的躁動。有了這個意識,活動度才能帶著我們真正往深處走。
這個意識,瑜伽傳統裡稱之為 svadhyaya,持續、有意識的自我觀察。我更習慣說是「覺察」。
覺察不只是一種練習態度,而是 mobility 得以發生的機制。從關節,到呼吸,到心靈狀態,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層次。而這項技能,不論從事什麼運動,我認為都是讓練習者能夠長久走下去的根本原因。不只是避開受傷的保命符,更是在表面的成績、看得到的「進步」、社群歸屬感等誘因退潮之後,還有理由繼續練下去的底層動力。
每種練習裡,都可以有覺察。這才是三本柱真正共同的地基。
我常和同學開玩笑:別和任何一家餐廳談感情,常換著吃,安全又健康。動作練習也一樣,不需要鎖定在某一種特定的運動或固定的練習方向。
只是玩笑歸玩笑。多樣和變化是手段,不是目的。能讓你練了二三十年還想繼續練的,從來不是因為好玩,而是因為每一次都還有什麼值得觀察、值得深入的事物在等著你。
那,就是覺察。
身為一個從瑜伽出發的練習者,我很好奇不同領域的人如何理解其他的運動類型。練重訓、跑步或者其他運動的朋友,能不能也跟大家分享你們跨領域練習的心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