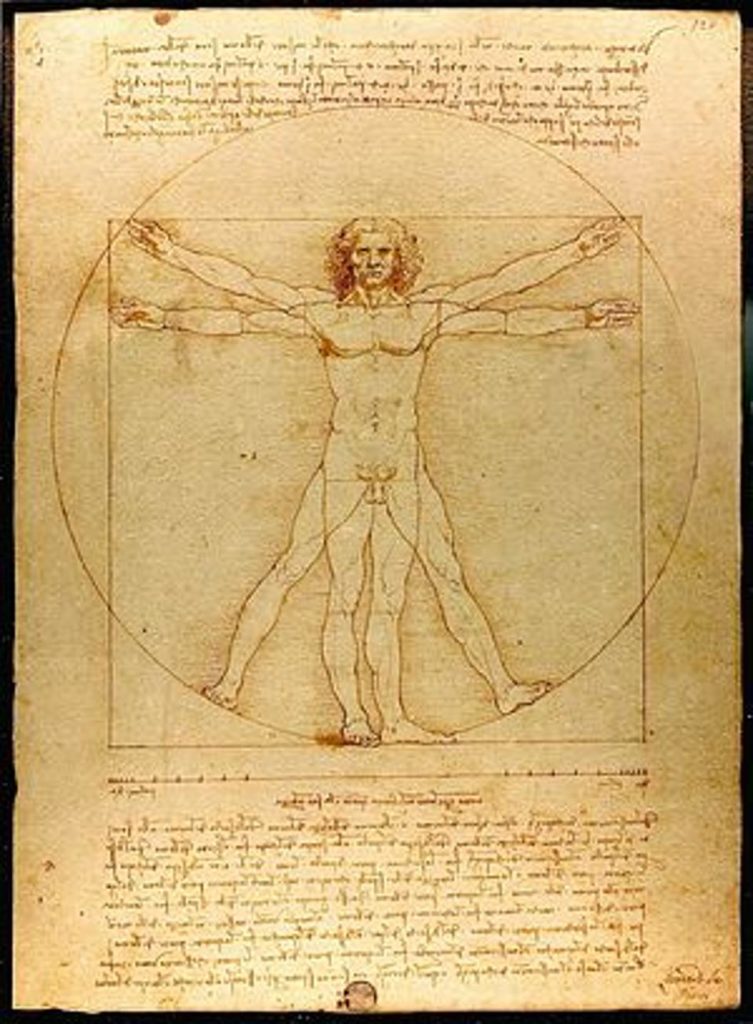每一趟旅程出發之前,不見得需要規劃清楚所有的細節,但總是得先想清楚要去的方向。方向搞錯,時間和力氣就浪費在冤枉路上。
不少人喜歡把每一堂瑜伽課比喻為一次「旅行」,但真的在踏上瑜伽墊、展開旅程之前,就先想清楚大方向的人,大概不會太多。
再簡化一點來看,就拿一個「動作」來說吧。
每一個動作都是由一堆姿勢、支撐點、移動的方向所構組而成。原本的支撐點或者地基在哪裡?構築夠穩定嗎?本來的姿勢是什麼,如何轉進、變化成要進入、停留的姿勢?如何看到似乎不見得具象的、「移動的方向」?移動的方向裡,呼吸是順著同樣的方向嗎?意念是順著同樣的方向嗎?
可能本來是站著的,就可以想一想,感覺看看,自己是怎麼站的,用什麼站的?(有人會說,「廢話,當然是用腳站」,話是沒錯,但實際的情況常常是只用一部分的腳,像是腳掌的外側,或者左右腳明顯不平衡。)坐著也一樣,怎麼坐?坐骨以外,還有哪些身體部位和地面接觸?左半邊和右半邊的狀態怎麼樣?即使是躺著,也一樣可以問問自己類似的問題。
好了,找到支撐點或者地基之後,就可以再問「要往哪裡去?」主要的方向是什麼?往下沉還是向上提?往前或者往後?要轉向右邊還是左邊?
除了要往哪裡去之外,還可以想想該怎麼去?有沒有別種同樣可以到達目的地的方案可以選擇?怎麼操作比較輕鬆,比較不費力?怎麼玩,可以看到更有趣的、或者更新鮮的風景?

如果是這種戰士二呢?夠歡樂嗎? XD (照片出處)
以戰士二(virabhadrasana 2)來說吧(我還是真愛提戰士二啊)。可以從山式(tadasana)當準備動作,可以從拜日式最後的下犬式進入,可以從側三角式(parsvakonasana)、三角式(trikonasana)、或者戰士一(virabhadrasana 1)、分腿前彎(prasarita padottanasana)再接著進戰士二;或者還有其他各種可能性。
哪一種進入方式,會讓我們更清楚意識到後腿的支撐?哪一種會讓我們更留意到身側的開展?哪一種給髖關節(哪一邊?)造成大比較大的壓力?哪一種會帶來剛剛好(或者太多、太少)的軀幹扭轉?怎麼做脊椎能最舒服伸展?怎麼做呼吸最舒暢?
不同的路線規劃,自然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。
即使是「進入」戰士二之後,方向的繼續延展也不會停止。兩隻腳掌的方向,前後膝蓋的方向,大腿小腿的方向,兩條手臂的方向、手掌的方向,骨盆、尾骨的方向,整條脊椎的方向,呼吸的方向。這些方向或者我們意識得到,或者意識不到,但都和我們怎麼想,怎麼設定,怎麼觀察密切相關。
重點是,我們知道方向嗎?我們意識得到身體的方向嗎?我們能夠真的想著(keep in mind)要去的的方向嗎?
再舉個例子吧。幾乎每堂瑜伽裡都會出現的下犬式,裡面的兩條手臂,走的是什麼方向呢?直覺想,大概就是就是往地面推出去、往前方推出去。有沒有可能,在下犬式裡的兩隻手掌,兩條手臂,不只是往外推,而且加上一點往裡收,加上一點接受、收納、收藏的念頭?讓雙手和雙臂有如從地面接受能量回到肩,回到心肺,回到臍,回到身體的最深處。
動態的姿動變化、動作有方向,那靜靜坐著呢?還是一樣有方向。能量在身體裡面如何流動?哪裡流得順暢,哪裡特別有阻礙?我們的念頭、意圖,能不能幫助能量的走向更順利、更舒暢?能量平順舒暢在全身流動之後,就可能再進一步看到更底層的心緒、意念怎麼流動,順著什麼方向流動。
找好立足點,想清楚要去的方向,然後就讓身體跑跑跳跳、讓心快樂飛翔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