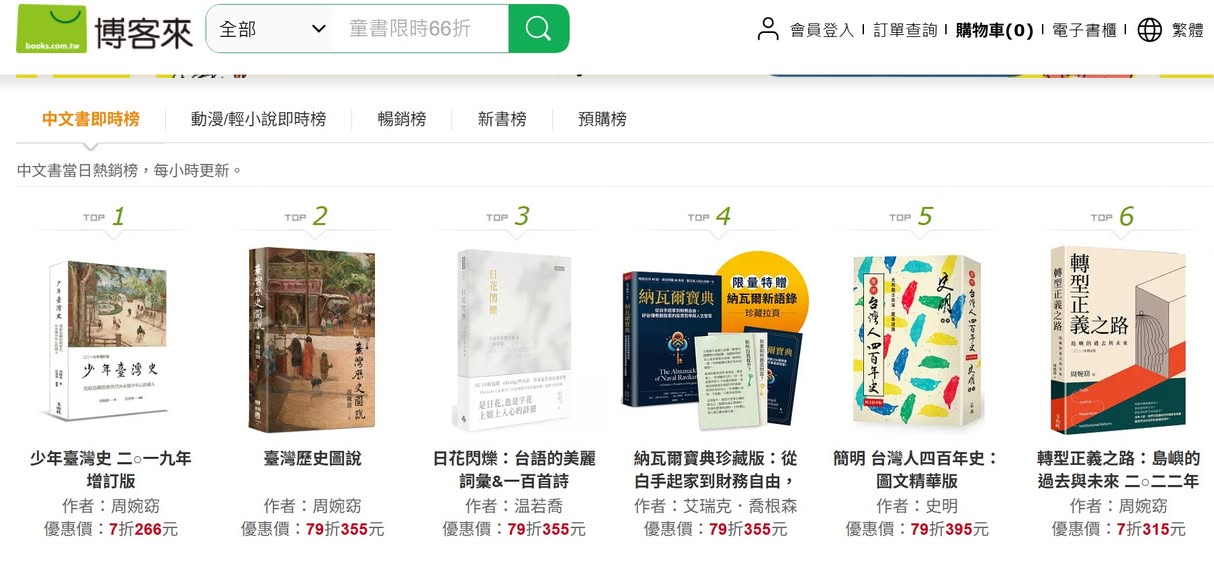閱讀長篇小說需要耐性,耗時耗腦,非常享受。過去一兩個星期,我利用捷運等車搭車、上課前下課後的空檔、上床入眠前十分鐘等等零碎時間,讀完了一本四百頁厚的長篇小說《北方森林》。
隨著作者的安排,慢慢欣賞故事場景的建構與開展,人物的交會。看著埋藏在故事背後的線察逐一匯整彼此接續,跟著作者的筆觸,像是跨越不同時代、漫步在繁華茂盛與乾枯凋萎次第變化的森林,戰爭與飢荒,愛情與背叛,特寫鏡頭與俯視鳥瞰的景緻與情緒交錯呈現。在畫面似乎漸漸明朗的過程,彷彿歷經了某種身心的洗禮:是的,我們就是森林,我們就是那一個一個悲喜人物的再現。知識與情感的強烈滿足,閱讀的樂趣就在其中。這樣的樂趣與滿足,與滑手機、看社群媒體、讀短文、看短影片,問 AI 一個艱難的題目而且在一分鐘之內就得到看似分析透澈、結構完整的答案,全然不可同日而語。
像是以傳統底片機拍攝一樣,得有耐心,等待,一整卷拍完,沖洗,等待,影像重新浮現在相紙上來到眼前。有人說儀式感十足,但只要操作過的人就都能理解,耐下性子,隨著時間的蘊釀,竟然能夠創造出如此驚人的張力、樂趣,與快感。
如今,全世界各行各業、股市都在瘋迷貌似萬能的 AI,到處都可以看到如何應用 AI 而快速完成工作的技巧。歡喜迎接眼前看起來美好的未來時,也有少部分的人對於這樣的發展,心裡或多或少存有些許疑慮。
AI 當然有不容忽視、抹滅的重大貢獻,有太多工作交給 AI 處理確時省時省力又省腦筋。但有些事,不親力親為,實在是浪費、實在是對不起兩足直立靈長類百萬年來的演化成果:頭腦與神經系統,結合四肢軀幹,精巧細緻運動(locomotion / movement)而來的想像力、思考、意識。
AI,究竟是福是禍實在難講,但終究會劇烈的影響我們的生活,這大概是確定的事。特別是面對各種大型語言模型來勢洶洶的誘惑,以及虛幻莫測的甜美承諾,我們需要更確切、更堅定的救贖。
以下羅列的習慣或技能,就像閱讀長篇小說一樣值得培養:
浸淫在自然環境裡。海邊也好,小溪流也好,郊山淺山深山高山都好,讓自己整個人融入到自然環境裡,眼睛看的,耳朵聽的,鼻子聞的,皮膚感受到的,沒有任何一種高科技能創造出這種等級的身心體驗。
和其他人的連結。朋友,親戚,談得來的都好。實際見面,喝咖啡吃飯喝酒,聊天,心情的交流,面對面看得見,眼神的交流,微笑,擁抱。即使是再怎麼內向的 I 人,也需要實際、親眼面對面的連結。
肢體的活動與探索。跑步,打球,重訓,攀岩,游泳,瑜伽,任何一種肢體活動都好,就像是每天需要三餐進食而得到的各種營養,肢體活動帶來的能量,也是每天都需要補充的。最低標準,一個禮拜兩到三次,一次30到60分鐘。天海祐希說得好,「男人會背叛你,但肌肉不會!」世界上沒有一種投資能比得上對自己肢體的探索與開發。
靜坐。每天五分鐘,十分鐘,半小時,一小時,找一處安靜的角落,什麼事都放下來,就只是站著或坐著。手機關掉,電腦關掉,聲音關掉,視覺關掉,暫時隔離掉一切外在的刺激,給頭腦一段斷食的時間,從頭腦裡放鬆,待在頭腦裡休息。只剩下自己,和自己的頭腦、自己的心面對面相處。這幾乎是 AI 時代最值得發展的習慣與技能。
其實還有很多小事情,像是拿出信紙,手寫一封信給好朋友,找出一張空白的圖畫紙,拿彩色鉛筆蠟筆水彩塗圖畫畫,唱歌給自己聽給家人聽給朋友聽,動動手給植物澆水換盆,撫摸家裡的毛孩。任何能用自己的雙手,用自己的身體,結合自己的頭腦、用心進行的活動,都能讓身心獲得滋養與感動,都能創造最棒的能量。
話說回來,我這兩天一邊趕作業似地繼續讀著生物學科普書《自私的基因》(超好看,必讀的經典),一邊忍不住開了新戰線,開始讀另一本篇幅較短一點的《軌道》,號稱就像是 Virginia Woolf 來寫太空似的那樣迷人的作品。似乎又是一段令人興奮的新奇旅程要開動囉!
#瑜伽老師讀什麼書
截稿後補充:
「有的人要相處一段時間之後,才能確定是可以長久交往下去的朋友。有的人,初見面,三兩句話,差不多就可以交心了。
之前讀的《北方森林》氣勢強勁,一開始讀即使如墜十里霧中,也因為作者暗藏而無法不流洩出的充沛能量,讓我乖乖繼續匍匐前進,曙光果真慢慢露出,甜蜜的閱讀快感,感性的、理性的,源源不絕。而現在的《軌道》,才兩三頁,我便俯首稱臣,強烈的共鳴感,一整個人和這作品的頻率共振。完全瞭解、信任。那筆法、想法、觀察,就是滿滿的同路人的氣味。無比安心卻又期待不已的旅程。
要如何說明我的喜愛呢?看了三五頁,我就確定之後一定要找出原文再讀第二遍。我有個檔案夾,專門用來存放很想再看、非得再看的書,我已經把這一本放在裡面了。」
補充的補充(星期天下午上課前,閱讀《軌道》讓我情緒能量超級飽滿,不得不發):
「何等的星期天。小寒,天氣回溫,暖陽,在街上吃了雞肉飯,買一瓶中藥理中湯,進捷運,找座位,背包裡掏出電子閱讀器繼續閱讀。到站,下車,電扶梯,再一段電扶梯,出站,暖陽還在。時間還夠,進了熟悉的咖啡店,熟悉的店員,熟悉的靠窗角落,暖陽還在。鄰座兩位外國年輕人,穿著短袖聊天。熟悉的店員端來我熟悉的咖啡。我已經回到閱讀。兩個太空人聊著他們在菲律賓潛水的經驗,分別看到哪些特殊的魚種。聊完後,她回想著母親年輕時在海灘上的照片。我抬頭看,陽光,陰影,四處張望與低頭的行人。磨豆機的聲音,咖啡機的蒸氣,店家的歌單裡一首一首八零或九零年代的民謠搖滾。對面的招牌,寫著『何等的咖啡』,每次看到我都忍俊不禁。何等的咖啡,何等的小說,何等的星期天。」
#瑜伽老師讀什麼書